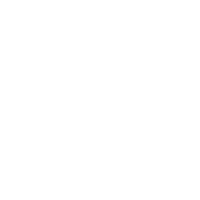采访、撰文| 唐飞
登上《时代周刊》
高治晓的手机来了提醒,还是那个单,在网上挂了几个小时,一直没有人接,他犹豫了一会儿,接了下来。
是个药品单。海淀区有个病人要买胰岛素,需要先去她家拿处方,到医院挂号交费,拿药,一趟下来得花去不少时间。那是2月,正是北京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他要去的是海淀医院,海淀医院是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为了避免接触,外卖统一要求放在医院门口的货架上,即便这样,骑手看到医院的单仍然“打死不肯接”。高治晓猜想这个病人可能正在等胰岛素救命,才一直没有取消。进了医院的大门,迎面而来是死亡的气息,空旷灰白的大厅,人们穿着防护服,带着护目镜,气氛压抑,他有些害怕。匆匆拿了药,走出医院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腿也在抖,他拿出消毒液,从头到脚喷了一遍,定了定神,跨上电动车,朝顾客家开去。顾客家在四楼。开门的是个清瘦的老太太,走路有些蹒跚,头发白了大半,但脸上全是笑容,亲切地招呼他进来坐坐。老太太给他倒了杯水,逗他说话。他送了那么多年外卖,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热情,那样感激他。他便进了屋,蛮不好意思的。听说老人还没吃饭,他起身去厨房下了碗面条,打了两个鸡蛋,给老人端过去。老人一个人住,他感到她是有些寂寞的,想有人能多陪陪她。他说,等疫情结束了,我再来看您,顺手把屋里的垃圾带了下去。因为这件小事,有位美国记者找到他,给他拍了一张照片。3月19日,杂志出刊,高治晓才知道他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那期的主题是疫情之下,世界各地的普通人。
(高治晓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照片中,高治晓穿着齐整的美团骑手工作服,佩戴头盔,口罩,坐在电动车上,露出了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一对浓眉,皮肤黝黑,典型的西北人的相貌。高治晓今年33岁,来自宁夏固原。2004年初中毕业后,他来的北京,他想北京是首都,不管干什么,在乡亲面前也算争了脸。他什么都肯干。2014年他在饭店做厨师,一天挣两百元,听说外卖员一天竟然能挣三百多,他就买了台电动车,下了班便出去跑外卖。一般是中午两点下班后,他去送外卖,送到下午五点,去饭店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后,再送几个小时。干了一段时间后,高治晓辞了饭店的工,成为一名专职骑手。骑手分为专送与众包两类,高治晓属于众包骑手,平台把业务外包给他,他就纯靠跑单赚钱。众包的好处是自由,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坏处是没有保险,也没有补贴。除了送餐,他还会接一些跑腿,帮买帮送,代购鲜花药品,等等。有的顾客周末想吃海底捞,又不想排队,就会下单请高治晓排队,差不多排好了,顾客再过去。这样的单能赚十几块,二十几块,但消耗时间,一个小时什么也干不了,和送餐相比并不划算。高治晓最喜欢送药品、鲜花,或者是去超市买东西,耗时短,一般到店商家就已经把货物备好。送餐就凭运气。碰上一些大的饭店,顾客点个煲汤,蒸鱼什么的,大饭店一般都是现做,碰上堂食客人多,等四五十分钟是常事。三公里以内的送餐时间是三十分钟,碰见这样的单,他就会超时。超时扣五块钱,每天超时三单,会被平台拉黑十二个小时。比超时更严重的是差评,差评一个扣五十,投诉一条扣五百。超时、差评和投诉也会影响平台派给他的单量。高治晓最怕餐馆出餐慢。有一次,他接了一个奶茶店的单。那是个周末,奶茶店在做第二杯半价的促销,门口排了一条龙似的队伍。一杯奶茶他等了五十分钟还没拿到,客户打电话来催,他说他没办法,顾客等不了,申请退款。他一分钱没拿到,而且白白浪费了一个小时。今年过年,高治晓和妻子在北京过的年。年前,陆续有武汉的新闻报出来,他俩商量了一下,担心把病毒带回老家,这次就不回去了。2009年,高治晓在餐厅做配菜,妻子是那家餐厅的服务员,这个女孩和他的家庭背景相似,俩人都来自农村,女孩性格踏实,不慕虚荣,他想和她在一块可以好好过日子。2013年,他们结了婚。
(高治晓获得美团颁发的抗疫荣誉证书)
疫情期间,高治晓和以前一样送外卖。外地人都回家了,北京空空荡荡,马路上寥寥开着几辆车。人们不敢点外卖了,但也不敢出门,高治晓接的单主要是去超市代购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每天能接二三十单。妻子担心他,“别送了,能不能过了疫情再送?”他安慰她,“没事的,做好防护问题不大。”他说,疫情期间送外卖,不仅能挣钱,也能帮助别人,很有意义。
没有哪个骑手不超时,不被差评过
外卖骑手以年轻人居多。大部分人很早辍学,上到初中或者高中,他们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很简单,相比去工厂打工,骑手挣得多,而且多劳多得,似乎很公平。在北京,最顶级的骑手一个月能挣四五万,简直堪称业内传奇。怎么办到的呢?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速度。有的骑手一天能跑十八九个小时,摩托车、电动车轮番上阵。他们是把自己的命托付给车轮的人。叶涛今年21岁,在河南郑州跑外卖。他来自周口,念到初中他不想上学,那时他们村上辍学是一种流行,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叶涛的父母经营一家早餐店,卖胡辣汤、油条和八宝粥,说你不上学就跟我们一起做生意吧。辍学后,他什么也不干,在村里和其他辍学的小孩一起在街上晃荡,到了2016年,家人看不下去,“你不上学,啥也不干,天天在家待着干嘛呢?”他想上班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虽然他讨厌被拘束。他去了郑州,投奔他叔叔。有次在路边,碰见一个骑手,听说送外卖比较自由,工资也高,他就干起了外卖。早上九点四十,叶涛起床,起床后去站点开会。早会一般能到四五十人,在商场门口或者马路边开,喊美团的口号,“美团外卖,送啥都快!美团外卖,越吃越帅!”复习礼貌用语——“你好,我是美团骑手,我来取x号订单”,“您好,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再见。
”用酒精给餐箱消毒,同时把这个过程拍视频上传到平台。最后,站长会播报昨天骑手超时、差评、被投诉的数据,挨个点名,被点名的骑手觉得丢脸。但是,几乎没有哪个骑手不超时,不被差评过。这些是骑手必须经历的,工作历程中的小挫折。叶涛年纪小,贪玩,外卖干得断断续续,不想干了,他就跑回家歇着,中间还跟着老站长跳槽去饿了么跑了几个月。今年疫情过后,他回到郑州,继续干美团骑手,美团的单多一些,他租了一个六百元的单间,只能容纳一张床。他嫌美团三百元一个床位的宿舍不干净。他有个弟弟,弟弟刚刚成年,俩人一起住在那个单间,弟弟也是一名骑手。最近,在快手上外卖骑手最怕什么投诉,叶涛每天发一条工作总结的快手视频,向网友展示每天跑的单量,他给自己立了个目标,每天跑到六十单。一般他能跑五十多单,有时候运气不好,就说前两天,平台给他派的全是三公里以外的单,一个小时只能跑两三单,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跑了三十几单。还有几次,尤其是中午,因为订单太多,系统变得不那么智能,东南西北的单都派给他,有的商家出餐就要二十分钟,很容易超时。超时顾客就会给差评,也可能退款,原因通常是送餐慢、等太久、骑手无法配送,他就会被罚钱,最多能罚五百。
(叶涛9月9日的工作总结快手视频)
几个月前,他接了个单。一开始,顾客填的是单位地址,等他取完餐,顾客下班回家,又把地址修改成家庭住址。这个地址在郑州南边,他在郑州东边,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他对那边路线也不熟,打电话给顾客,说太远了,没法送。顾客就退款了,选择的原因是“骑手通知我无法配送”,他赶紧给商家打电话,说你别给顾客退款。他又给顾客打电话,说您不能因为这个退款,我要罚五百块钱。最后协商的结果是,他花了四十多元把顾客的饭买下,点了送达。还有一次,也是顾客修改地址,本来派送距离不到一公里,顾客修改完后,距离增加到两公里。等他取过餐,顾客打来电话说,我出门了,外卖不要了,要退单。叶涛说,商家做好了,肯定不会给你退。顾客说,没有办法,这单我给你,你吃了吧。说完挂了电话。叶涛只好又跑了两公里,到顾客家点了送达,然后把那盒饭吃了。叶涛也点外卖,那是他每天的最后一单。他会给自己点一份外卖,再把单接了,这样既能吃一份饭,还能赚到五块钱的配送费。叶涛每月收入七千到八千元。按说应该吃穿不愁,还能有结余。这几年,他一直没存下钱,他喜欢去酒吧喝酒,也喜欢去外地旅游。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对过于沉重的生活总是有些抗拒,赚了钱就忍不住要花出去。去年,他买了一辆十七万元的大众汽车,首付八万多,每个月还三千二百元的贷款,这样一来他的经纪压力便大了起来,更存不下钱了。那辆崭新的大众汽车在路边的停车场停了两个月,他没开过,总不能开着车送外卖吧?当初,他被一股冲动的虚荣蒙住了心,看见有骑手买了车,他也想买,“反正结了婚也要买车的,早买晚买迟早要买。”他就没想到结婚首要的大事是买房。骑手叶涛就这样被一辆车困住了生活。一个教训。叶涛说他挺后悔。
彝族女孩变身嘉兴跑单王
《人物》杂志对骑手的报道发出后,很多骑手在朋友圈转了这篇文章。小黑在朋友圈转发说:“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看到这篇,心里隐隐作痛。”小黑在饿了么做骑手。有一次,平台同时派给她六个单,全都要在三十分钟内送达,光提前送达她就点了三单,压力特别大,“一点不人性化,他们就把我们骑手看成工具,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人,更不会把我们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回到凉山,穿起彝族服饰的小黑)
小黑是个女孩,今年23岁。小黑来自大凉山,是彝族人,小麦色的皮肤,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元气十足。16岁,经媒婆介绍,她和一个男孩谈恋爱,随后移居到浙江嘉兴。婚后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在她看来,她的婚姻是一场巨大的失败,因为丈夫是个“废人”。她丈夫也是个骑手,早上七点半出门跑活,晚上七点下班,从来不加班,一个月赚五千块钱。对于丈夫的工作作风,她很生气,“多跑点单也不会少一块肉,也不是不给你钱,而且下班回来还不是在家玩手机!”小黑和丈夫不一样,也可以这么说,她和她丈夫根本是两种人。虽然是全职骑手,但小黑没有底薪。在嘉兴当地,900单以下每单收入4块,901单到1200单每单4块5,1201单到1800单每单4块6,再往上每单4块7。因为多劳多得,小黑每天从六点开始跑单,一直跑到夜里十二点,能跑八九十单,一个月能挣一万,一度成了嘉兴的跑单王。
为了节约时间,她只吃早饭和晚饭,早饭吃包子面条,晚饭吃盖浇饭,最喜欢吃青椒肉丝盖浇饭。最疯狂的一次是2018年的春节,那年二月,二十八天,她跑了两千多单,赚了将近两万元。春节的单价高,一单十块钱,她从早上八点跑到夜里十二点多,不要命了似的。电动车车速开到六十迈,从一楼爬到六楼,只需一分钟。她的手上一直在爆单,有时一次能挂十几单,压力极大。但她扛住了这份压力。外人不理解小黑为什么这么拼,况且她是个女孩,丈夫不心疼吗?想起丈夫,她就伤心。2015年,她怀孕,生完孩子后,她生了痔疮,孕妇很容易生痔疮,在医院看病花了三万多。那会儿她在一家玩具工厂包装玩具,工作清闲,一个月赚四千多元。怀孕后,她没再工作,丈夫也不挣钱,房租没钱付,连小孩生病去医院也没钱。在医院,没钱买饭,她饿了三天。她想吃香蕉,从家里搜罗出九毛钱,买了一根香蕉。那次之后,她下定决心,要拼命挣钱,决不允许再沦落到这个地步,“就算自己的男人不行,我要把自己的那份责任扛起来。”
小黑记得送外卖的第一个月,她不熟悉路,找不到地址,经常急得眼泪直流。有一次,她手上有四五单,到了小区后,她绕来绕去都找不到顾客地址,绕了一个小时,她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等到顾客家,面条都糊掉了,根本不能吃了,她哭着敲了顾客的门。顾客说,面糊了不要了,她只好自己掏钱把单买了。除了过年,她几乎不休假。彝族是11月过年,她会回大凉山待一个月。回到家乡外卖骑手最怕什么投诉,她才能彻底放松下来。每天种种田,弄弄地,穿上盛大的民族礼服,参加亲友的宴席。短暂的休息后,回到嘉兴,她又变成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外卖骑手。
(小黑在雨中送外卖,来源:快手视频)有一年,饿了么给员工休一个星期年假,每天有一百元补助。她去了上海,看见了经常在电视出现的东方明珠,坐观光电梯,从高处俯瞰外滩,觉得不可思议,想这是上海啊。她喜欢上海,喜欢那些优雅而古老的建筑,可只待了两天,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去送外卖了。有时候,小黑不免会想,她不会一辈子送外卖,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喜欢因为争分夺秒而带来的速度感,就像玩一场刺激的游戏。在快手,她有一千多个粉丝,有网友留言说,“你是我见过最美的骑手,也是最厉害的骑手。”也有人看见她在视频里哭,讽刺她:“如果你吃不了这个苦,就不要在这里哭。”她想,也许有一天,她会离开嘉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学一门乐器,她觉得做一名流浪歌手挺浪漫的。
“除了拿餐就是送餐”
在东莞的骑手蒋章世和小黑一样,因生活所迫从事外卖行业。蒋章世今年三十岁,湖南人,今年五月开始做专送骑手。他的妻子怀孕了,预产期是十月,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这一胎生男生女都行”。在这之前,蒋章世在牛肉连锁加盟店卖牛肉,后来去了酒吧做市场经理,疫情之后,酒吧关门,他只好干起了外卖。卖牛肉那一年,他赚了不少钱,白天卖牛肉,晚上他和朋友打牌,打通宵,结果把身体打坏了,腰间盘突出,不能行动。他回湖南老家休养了一年,吃了一年中药才好,只是不能再干重活。腰病至今困扰着他,他只能睡硬床板,有一次,因为赶时间,他送餐送得太急,闪了腰,那一整天他不能直起身子走路。
(蒋章世的快手视频截图)蒋章世送的是夜班,从上午十点送到凌晨四点。经常熬夜,白天他时常感到疲惫,有时会眯一会儿。但是高峰期,也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绝对不能休息。之前在酒吧,他也上夜班,下午两点拓展客户,晚上带客人去酒吧,一直陪到客人离开。他在美团上班,前三个月没有补助,一单五块钱,过了三个月,能涨到一单五块一毛钱,或者五块两毛钱,还有话费补贴、车补、高温补助,差不多五六百元。他每天能跑五十五单左右,加上补贴差不多有九千元。即便如此,他在东莞只租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单间,孩子和妻子都在老家。之前妻子会过来,给他做饭,洗衣服,最近妻子快生产,他就让她回老家休息。和大部分骑手一样,蒋章世的生活单调死板,乏善可陈,“反正送外卖,每天上班十五六个小时,不辛苦不累是不可能的,基本上跑美团一天除了拿餐就是送餐,没有时间出去玩,除非你生病,生病你还要出来跑一两单。”
(蒋章世在快手说,送外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需要乐观主义,为商家所想,为顾客所想)在骑手中,高治晓属于心态平和的那类,他规定每天跑够四百元,就回家休息。他很少闯红灯,“订单超时了,我都会想着超时就超时吧,就扣一半钱,如果让车撞了,不是更麻烦吗?”两个月前,一个丁字路口,他看见一个骑手因为速度太快,被撞翻在地,脑袋着地,地上流了一摊血,车上的牛奶、鸡蛋全洒了。看到这一幕,他特别心痛,“感觉心脏都不由自己控制了。”他告诫自己,不要重蹈覆辙。高治晓想有个孩子,但他不敢对未来期待太多。2019年,他离开北京,去了福州,用积攒的十几万开了一家饭店,还借了几万元。他的表姐在福州开厂,说那里可以做外地人的生意。他动了心。饭店主打川菜,有一百多平,前两个月生意挺好,后来那一带饭馆越来越多,他的店渐渐无人问津。福州人也不喜欢吃辣。眼看生意萧条了下去,他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坏,经常吵架。他不适应南方的天气,连绵不断的雨,空气能捏出水来。“为什么每天要受这个罪?”他问自己。一年后,他把饭店清盘,回到北京,又成了骑手。高治晓经常会想起母亲。母亲七十多岁了,住在大哥家,帮大哥照看孩子。他大哥有癫痫病,生活不能自理。听说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很有名,他一直想带大哥来北京看病。他仍想开一家饭馆,也许不用那么大。他觉得北京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城市,“只要肯干 ,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都有机会有渠道挣钱。”偶尔,在北京,他会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有一次,他送餐到清华大学,当时口罩紧缺,一只口罩他戴四五天舍不得扔掉,顾客便拿了两个口罩给他。那天天气寒冷,风很大,还下着雪,他感谢了那位顾客,换上新口罩,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中。
免责声明:部分文章信息来源于网络以及网友投稿,本站只负责对文章进行整理、排版、编辑,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本站文章和转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及时联系本站,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