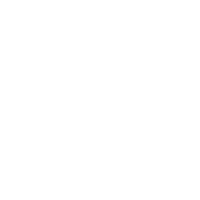这一年,做了近7年外卖员的陈流向外卖平台客服“投诉”次数频繁了许多。
近来的一次,是他认为平台派顺路单时规定的送餐时间不合理,引起他配送超时。
“前后3个单子分派给我的时间相差6分钟,都要让我在45分钟内送完,如何可能?”他在投诉电话里反诘。
“外卖越来越难送了。”这是去年开年之后,不少外卖骑手的普遍体味。
在往年的报导中,外卖骑手们大多被形容为一群困在系统里的人。新乡学院文大学院士邢斌曾在2022年冬做过1个月外卖骑手。他提到:“外卖工作没有前途,是一种十分乏味、天花板特别低的纯粹重复的体力劳动。”
但是,我们访谈了近30名职业状态不尽相同的外卖员,发觉她们的职业态度与选择正在转变。骑手并非只会默默接受系统派单的工具人。她们有人是刺头,遇见bug就投诉;有人决定“不惯着系统”,做自由的玩家;还有人尝试与平台对话……
事实上,“作为平台,也期盼老骑手才能通过‘养系统’来增加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建立和更新数字技术。”美团一位算法负责人表示。
外卖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但仍有越来越多人涌向本就拥挤的赛道……与系统的不断磨合,亦是依赖平台经济迅速扩张的新职业群体面临的真实境况。
陈流在送餐。杨书源摄
单越来越难跑?
半夜10点多,10多位骑手散坐在广州宝山区一个大超市的广场椅子上,沉默地刷着手机,屏幕逗留在外卖骑手APP抢单大厅页面。
系统早已阔别了近10分钟。“像是睡觉了,连个鬼影也看不到。”陈流(化名)打趣。
那天,那位42岁的美团众包全职骑手还没有完成自己定下的目标,“起码挪到300元”,但他准备再坚持一会儿。
“呲——”一位骑手送餐归来,重重踩下煞车,喊了句:“又送了两个垃圾单!路绕得要命!”他的反应引爆了话题,好几个骑手开始数说不顺利的送餐经历。
在骑手们的手机APP抢单大厅,95后美团乐跑团队骑手蒋海龙也看出了疲态:原先三四十分钟都没人抢的单子不见了,如今无论是哪些外卖订单,一上线就“秒没了”。进餐高峰之后,抢单大厅里挂着的几乎都是几小时后的预约单、跑腿单。
骑手们想要维持原先的双数,就得降低工作时长。“我如今每晚跑40单要花9个小时,之前6个小时就干够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骑手埋怨。
专送骑手的薪水是周结,相对也比较固定。某平台的一位专送骑手追忆:“前三年,同样的均价,例如曾经跑500单,能有4000元的收入,现今差不多就3500元。”在记者访问的近30名骑手中,从业一年以上的骑手都表示“今年收入比以往增长了”。
陈流曾经最爱在洪水天送餐,平台对于骑手在洪水、高温等极端天气,挪到固定的双数后会有一定奖励。但近来几个月,风雨天气的津贴越来越少了。
为了获得带教奖励,陈流收过几个师父。若果这种师父入行20天内能挪到400单以上,陈流能够获得数百元。但逐渐,陈流发觉收到的补助和时间投入不成反比。“我上一批师父,10个人里只有3个完成任务了,我还要时常帮她们去送快超时的外卖。”渐渐他也不再收了。
跑单的难度却有增无减。好多骑手在系统里获得的顺路单跑上去“越来越不顺路”:“虽然在一个大方向上,而且各类转弯,如同树枝一样,非常容易超时。”一位早已入行3年的骑手埋怨。
跑单艰辛,让陈流对系统固有的漏洞显得更加敏感。“为什么系统测算的骑手里程数仍然不准,有时侯要少算将近一公里?”
“如果系统里的bug仍然没有反馈,那我就带着我的师父们全都到另一个外卖平台去。”他向所在站点的站长放言。
“不能惯着系统”
一次次的公开抗衡,让陈流成了站长眼中的“刺儿头”,而更多年青骑手和系统之间的“斗智斗勇”,隐蔽却愈发有效。
“那些跑得成功的都和我说过,不能太老实,不能惯着系统。”下午1点多,32岁的骑手小迎把送餐的电池车停靠在某商圈一个有绿荫的十字路口旁,慵懒地半躺下。一个晚上跑了十几个单子,效率不错。
小迎离开外卖行业1年多了,开小店创业赔钱后,明年初刚回归。重新做骑手后,一切清零,他的骑手帐号“还没有养大”。
“养号”,是骑手行业的“黑话”,指的是骑手必须不断通过高效接单、拒单,让外卖系统晓得自己的送餐路线偏好,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系统派单路线。
小迎艳羡这些“把系统养得好的骑手”。“一个远单抢出来,同一个方向的顺路单能派上三四单,七八十元就到手了。”
“等级越高的骑手,系统对他的评估能力越高,同时能给他派的顺路单就越多。最厉害的,一次同时可以挂八九单。”小迎解释。如今他的骑手等级是“荣耀精英二级”,“这就和游戏里升级一样,等级入行时升得非常快,前面升级都会很难。”
把外卖员当作全职,和勤劳接单同样重要的是学会适时拒单。“如果你想好了一个方向,就都往这个方向跑,其他单子都拒掉。”
与之相对应的,骑手圈中还有“垃圾单”、“单飞”的概念。“垃圾单”指的是这些难找或则是没有扶梯的高层业主的外卖单,而“单飞”则指送餐中途没有顺路单、来回一趟十多公里可能只挣一笔外送费的情形。
“垃圾单可以转单,每晚最多能转出8单,其中5单免费转,3单需加钱,为了让人拿走你的单子,你也可以为这笔单子加钱,8元封顶。拒单没有双数限制,但三天控制在20单左右则没有大问题,假如过多,当日系统就不会再给派单。”这是饿了么外送平台一位众包骑手介绍的经验。根据各个平台以及骑手所属的方式、团队不同,转单、拒单规则不尽相同。
一次,小迎瞥到一个在他身边仓促出发的骑手的等级早已达到了“战神”,他摇头小声笑着说:“这样的骑手不是最厉害的,可能反倒证明他哪些垃圾单都接,才能得到这个封号。”
蒋海龙也多少晓得这种外卖员的生存法则。送餐时他听到一些新骑手在公路复杂的社区里一脸无助,或是联系不到客户时满身沮丧,就想为她们提供一些经验。
蒋海龙在骑手社区里发表的经验分享帖。受访者供图
从今年开始,蒋海龙相继在骑手的线上社区发布了一些送餐的经验贴,累计已有十几万的点击量。经验帖里,“骑手怎么能够高效送餐、避免超时”是点击率最高的命题。他有时也会教学有效借助拒单、转单的小方法,以及违法行为被平台交纳津贴后的申述技巧。
还有些经验,只适宜口口相传。诸如骑手高峰期忙乱,若和别的骑手拿混了餐品,应当如何处理能够免予客户的投诉和平台的惩罚。
“收到”“好的”——骑手们在看完后,大多会留言寥寥几句。像是在人与算法的博弈中,达成的一种默契。
说“不”真的有用吗?
从平台的回复来看,系统虽然欢迎骑手说“不”。
任何一个订单背后都有三端的需求:用户希望早点吃上饭、商家希望一出餐就有骑手拿走、骑手希望接到的都是顺路的订单并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
一位美团平台的算法负责人解释:“算法的本意是为了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兼具用户、骑手、商家三方的体验。外卖菜鸟前期对算法不熟悉,对算法的吐槽也可以视为‘磨合’过程。并且作为平台,也期盼着一个老骑手才能通过‘养系统’来增加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建立和更新数字技术。”
按照美团平台的统计,自2021年至今,平台已做过7次算法公开和改进,包括公开“预估送达时间”算法规则,选择其中最长的作为最终的订单送达时间,将“预计送达时间”调整为“预计送达时间段”;启动“出餐后调度”试点,店家通过免费领取的终端“出餐宝”,上报出餐情况,出餐完毕后,后台再调度骑手到店取餐;在试点城市,对骑手收差评、超时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骑手可以通过安全培训、模范事迹等加分项进行填补;向骑手推送出餐提醒、推荐“建议到店时间”等。
也有一些改变并不受骑手欢迎。
好多众包骑手追忆,从去年5月开始,一家外送平台出了新的规定外卖骑手最怕什么投诉,众包骑手每晚只有最多拒绝10次平台派单的机会,而原先骑手拒单是上不封顶的。
事实上,骑手们十分明白,在越来越多人涌进赛道,有一些情况是说“不”也解决不了的,由于符合市场客观规律。
例如为什么骑手饱和了,每位站点的人数还在降低?“区域总监、站长招的骑手越多,每位骑手撤单就少了,责任区内超时单量越少,取消和差评量也越少,那他薪水就高。但这对靠单量喝水的骑手来说就意味着低总价,抢单难。”一名众包骑手了然其中逻辑。
在向平台的人工客服投诉后,陈流常常得到的是程式化的回复。“普通用户点餐遇见了问题,也是打这个客服电话,我们也没有专门内部的骑手通道。”这种时刻,他总会掠过个念头,“平台并不是我的老总,我和这些点外卖的人一样,就是一个用户而已。”
而蒋海龙则会找寻一些非常的机会。平台有时会和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一些新职业群体的座谈会。近来一次的座谈会上,他提出一项关于“骑手派单机会公正”的议案:建议系统后台降低对跑单收入常年高于平均水平的骑手做甄别,剖析是否因为派单机会不公造成了她们收入低,为她们提供更多派单机会。目前,议案还在递交处理中。
自由与归属
外卖骑手们究竟是被困在系统里,还是把握了与系统对话的能力?专访了30多位外卖骑手后,记者发觉年纪虽然构成了一条微妙的分界线。
对还没到30岁的小迎和蒋海龙来说,她们没感觉自己困在系统里,喜欢的是做骑手的自由。蒋海龙是北京本地人,2017年大专结业,学的是车辆修理,并且去鞋厂实习一周后就离开了,“我不想过那个流水线上的生活。”
“做骑手就是为了追求自由,那里钱多去哪儿。”小迎说。
在记者专访的其他30岁以下的年青骑手中,外卖员也大多并非她们的第一职业,更像是一块跳板:有的人以前创业开店;也有年青骑手反复在“众包”和“专送”骑手间横跳,中途遇见了别的机遇,才会离开骑手行业一段时侯。(“专送”,指全职骑手,由劳务公司以团队方式管理,有愈发稳定的系统派单;“众包”则愈发自由,收入上相对不稳定。)
“我们年青一代的骑手,也有不少读过学院,甚少有人是由于生计所迫做骑手的,大多都是为了工作的弹性和自由。”蒋海龙说,真正被动的是这些40岁以上的中老年骑手,“他们很难再被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行业接纳”。
在做骑手之前,陈流是鞋厂的技术工,一干就是12年,最后做到车间书记,手下管五六十个工人。7年前改行,正是外卖行业的颠峰时期,陈流月入能轻松过亿元。“回村里,和他人说话嗓门都大一些。”因家事和母亲谈不拢,二人以结婚告终。3个儿子都判给了相对有经济能力的陈流。
收入增加后,陈流也想过改行,并且做哪些呢?原先的鞋厂是做新能源风力发电,他负责生产一种油压的管线,出了厂几乎很难再找到须要这些技术的工种。
在对站长放狠话后,陈流也没有勇气真的换平台,由于哪个平台每单的均价比现今的还要低近1元。
小迎见过不少年纪大的众包骑手最后转为专送骑手:由于抢单普遍抢不过年青人,只能借助系统派单。他50岁的儿子,在另一个外卖平台做专职骑手近10年。这个平台创立早,但骑手的送餐总价很低。“你敢信?爬六楼送一单只有4元”,小迎总劝丈夫跳槽到自己的平台,但父母舍不得,“他总认为他属于哪个平台的专送骑手,愈加有保障。”
归属感是40岁以上骑手更在乎的事。
9月初,3个儿子相继开学,将近两亿元的杂费,陈流只好找熟人借,一下子负债1万多元。为了早日还债,他决定再度申请加入的“乐跑远骑手”队伍。陈流总结乐跑骑手是在众包骑手中“挑选好的、守规矩的”。今年他也加入过一段时间,收入稳定在1亿元出头,但由于好几次和店家因出餐速率问题发生口角外卖骑手最怕什么投诉,半年后被清退了。
经过2个月周折,他终于转岗成功了。
但他先前的站点没有乐跑骑手团队,他必须转岗到更偏僻的站点,还得舍弃早已跑熟的片区、积累的店家人脉。并且,成为乐跑骑手后,工作中的规矩会变多:每周要去站点开两次会议、送餐的时侯必须穿美团规定的服饰、定期被检测是否戴好安全帽……
但“刺儿头”陈流却时常形成了一种从前在鞋厂才有的、久违的归属感。“每个队伍都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马刺长带着你,一个星期发一次钱,薪水也更存得住,曾经跑单日结,更像临时工。”
陈流在送餐。杨书源摄
归属感,也意味着保障。年龄大的骑手们最关心,送餐途中的意外伤害,该谁来埋单?
前段时间,陈流送餐时从电池车上摔下,小腿疼了快一个月。“能走路,代表没有伤到腿骨,就是皮创伤。”只休息了1个小时,擦了些双氧水,他又重新上路了。从这天起,他总认为跑得急了,重伤的腿会嘶嘶嘶嘶发出脆响。他开始尽量避开这些爬五六楼的单子,“腿总要省着点用,花不起医药费”。
每晚复工时手动交纳的2元多商业保险费到底有哪些用?陈流不清楚。“我晓得的是300元以下的医药费都不给报,我买点药可能就五六十元,能赔吗?”总认为是在给自己打工的陈流毫无胆气。
去年陈流隐约听其他外卖员说起,平台要给外卖员买新的保险了,“这个保险保障的东西愈发全面”。他口中的“新保险”指的是,自2022年7月至今年末在广州、上海等地试点的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由人社部门牵头施行。7月份,全省超过100万名骑手获得了职业伤害保障。即使陈流早已被列入了保障人群,但由于这份保险不须要骑手收取,他也不了解这份保险该怎么定损。
在谋生与职业之间
2年多后,蒋海龙被升为了骑手团队的勇士长。团队里有了30多个骑手。从那时起,他开始思索一些更深的问题。
“我和平台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样的?我是平台的雇员还是事业伙伴?似乎都不是。”
2023年旧历春节时,蒋海龙所在的月浦镇社区负责人来督查。他提出了一个酝酿已久的看法:是不是可以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掏出一小间房,作为骑手的休息驿站?他想掏出1500元的骑手奖励金,购置冰箱和果汁、零食。“骑手算半个自由职业者,有时很难找到社群的归属感,假如有这样一个小屋子,也是一种抚慰。”
不足10平方米的骑手驿站建上去后,蒋海龙把每周一次的骑手会议放在了驿站里。周边的骑手们不忙时就会来里头坐坐。驿站里相继也有附近企业捐来物资。骑手们常取走的不是好几元一瓶的啤酒,而是果腹的面馆包。
去年末,蒋海龙报考了平台提供的去开放学院免费读现代货运管理专业的机会。
蒋海龙在自己呼吁的社区骑手驿站内。张玮摄
骑手是一个“天花板”轻易可见的工作:2022年美团配送即时配送平均每单成本是4.53元。在美团外卖骑手端APP,会显示各个城市骑手单量排名榜,通常的城市亚军三天可以挪到140-150单,每晚的收入在675元,虽然跑满30天,虽然达到体能极限,每月收入也不会超过2亿元。
免费的网路成人教育到底能给蒋海龙带来哪些?他并不清晰。不过报考念书时,他下载保存了一张平台制做的美团骑手的成长路径示意图。在这张表格上,他听到了站长、客服、培训师、招聘专员这种字眼。在开放学院里,他也遇见过结业后晋级为区域总监的骑手师弟,“起码这是上面的人走通过的路。”
虽然嘴上不认同母亲,但小迎有时也会感遭到作为众包骑手的“飘浮感”,例如时常想起一年四季的骑手服都要上平台花钱去买,他总有些不甘愿。
蒋海龙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发起成立的骑手驿站。杨书源摄
直至10月初,早已加入乐跑队伍的陈流还没有完全渡过经济危机:每晚的跑单量都是刚才达标;生活由于还债捉襟见肘。本来应当在平台上买春天的骑手工服穿了,他舍不得,干脆直接在夜里跑外卖时,套上冬天的工服。几单跑出来,风吹在脸部冰冷,身体却是一片疲乏。
虽然如今收入不如从前了,但陈流对刚入行的师父说的还是这个行业的“好话”:“我在村里只读到初中结业,刚开始送外卖时,还挺粗暴的,扯着喉管在门外对顾客喊。”所以现今无论是餐品洒漏还是送餐迟到,他都有了自己的一套处理危机办法。
10月初,蒋海龙收到了一个让群里不少骑手都有些激奋的消息:骑手吴伟双成功申请到了2000多元新职业伤害保障赔付。5月,吴伟双在送餐回去途中,为了避让汽车,在制动时跌倒了,被确诊为左小腿、右手软组织损伤。那种月,在吴伟双所在的宝山区,一共受理了10起类似的职业伤害保障定损。
如今,蒋海龙仍然会掠过刹那间的疑虑,“如果仍然留在外送别业,深造后真的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吗?”但很快,这些看法才会被派单系统里新订单的语音提示覆盖了。
骑手送餐的背影。杨书源摄
上一篇:北京多家商场堂食不再查核酸不扫码
免责声明:部分文章信息来源于网络以及网友投稿,本站只负责对文章进行整理、排版、编辑,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本站文章和转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及时联系本站,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